放棄“產能至上”的尚德模式,一步步深入市場終端,默默無聞的中盛光電耐心地等待機會成長為新一代的光伏明星
“你知道為什么嗎?因為他清楚,我能夠卡住他的脖子。”
說這段話時,王興華的臉上沒有一絲殺氣。相反,笑容讓他本就不大的眼睛變成了一條細線。
故事發生在幾個月前,那場橫掃全球光伏產業的寒冬正在最寒時。對話的雙方是中盛光電董事長王興華和江蘇省一家光伏組件上市公司的老總。“你把我收購了吧?”對方突然一語讓王興華一驚。
“你是美國上市公司,我還沒有上市。你的市值比我的總資產都大幾倍,我拿什么去收購你?”王興華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管收購不收購,反正以后就跟你混了。”這是該“名人”(王興華強調)的回答。
這個我們今天無從考證的橋段似乎是在證明王興華的狂言。“我們是中國最獨特的光伏企業。”身材不高,微微發胖的他對《創業家》說。但2008年不足70兆瓦的光伏組件產能并不能支撐他的“牛皮”,這個數字幾乎只是無錫尚德的十五分之一,天威英利的四分之一,天合光能的三分之一。
而王興華所顛覆的正是“產能至上”――這個在中國光伏產業中被奉為圭臬的概念。
追日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技術型的制造企業。”王興華說這句話時距離北美最大的追日系統電站竣工還有4天的時間。4天后,美國加州財政部長親自出席了這場竣工儀式,這座電站使用的全部都是中盛光電的追日系統,一共97套。
“中國光伏產業繁榮的本質是什么?就是買設備,上產量,簡單地重復生產。有幾家企業有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王興華的追問直逼中國光伏產業的命門。但是,從組件向上游走,研發的重心是電池效率和硅料提純,難度非常之高;而向下走是系統集成,相比之下,這里的研發要容易得多。王興華于是選擇從系統集成切入。
2006年,中盛組件廠投產剛剛一年,王興華就開始開發伺服系統。他首先找到了一家有技術基礎的西班牙公司合作,但不久他就發現,西班牙人的技術惰性很大,對革新的欲望非常弱。“我們覺得不行,于是就在它的基礎上,自己全套重頭開始來做。”8個月之后,中盛第一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雙軸追日系統研發成功。到現在,他們的第三代產品已經上市。至今,中盛仍然是唯一一家能夠生產雙軸追日系統的中國公司。
在國際權威光伏雜志《Photon》2008年10月推出的榜單中,中盛的追日系統在關鍵的抗風性能上位于世界第一,轉換效率排名世界前三。美國一家電站業主也曾經做過一次實驗,把全球若干家伺服系統廠家的產品放在一起運轉,最終的實測結果是中盛的發電效率最高,比固定式系統高出了44%,比單軸追日系統也高出了20%。
從2007年第一款產品D80推向市場以來,中盛累計向歐美市場銷售追日系統上百兆瓦。“組件的利潤現在已經歸于平均化了,但追日系統的利潤還能達到10%以上。”中盛副總裁、美國分公司總裁眭林輝告訴《創業家》。
“在美國雙軸追日系統還是一個非常新的產品。”眭林輝說。有多新?上文提到的北美最大的追日系統電站招標時就直接采用了中盛的系統數據。新意味著什么呢?“組件商賣出去的是什么?就是一塊板子。電池板已經是標準化的產品,每個工程商都會安裝。但我們的追日系統很新,沒有人熟悉它的安裝技術。”
事實上,不僅僅是安裝,一個追日系統電站從項目規劃開始一直到建設完成都需要中盛全方位的技術支持,從電站的土壤分析、地震帶分析、系統排布方案、電站發電量計算,直到指導安裝。“我們拿設備提供商的錢,但幾乎干了工程開發商(EPC)所有的活兒。”佘海峰說這也構成了他們后來商業鏈條向下延伸的重要動力。
正是由于業主對中盛的高度依賴,使得中盛在美國甚至扭轉了光伏行業的一般產業流程。傳統上說,業主只需要找到EPC,后面工程就是EPC的事情了,而設備商只和EPC打交道,不需要知道業主是誰。但現在業主在投資前就必須要出面找中盛了,因為EPC不會根據追日系統來為業主計算投資回報率。“現在很多時候是我們和業主談好,再由我們找長期合作的EPC進來。”眭林輝說,“全反過來了。”
“反過來”的結果是中盛對項目源有了更強的控制力。最近中盛剛剛中標加州一個35MW的項目,對方業主甚至寫信邀請中盛自己來做EPC,但中盛美國公司考慮到自己的經驗不足,婉言謝絕了。“這是一個總共100MW的項目,如果合作愉快,那么后面的工程就還會給我們。”
美國光伏電站項目中70%是通過PPA(電力購買協議PowerPurchase Agreement)的方式來完成的。項目公司從大投資人手中拿到資金后再用“零售”的方式去購買電站項目。現在中盛已經和美國所有非競爭性PPA公司建立了聯系。顯然,對于剛剛啟動的美國光伏市場來說,中盛已經找到了開門的鑰匙。
然而,伺服系統的成功并沒有讓王興華滿足,他知道這還不是能“卡人脖子”的技術。那么什么才是他眼中的撒手锏呢?“電站技術是我們未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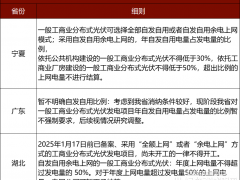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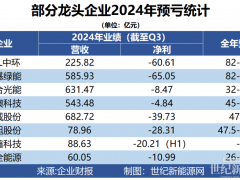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