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幢屋頂都是一個迷你發電站,一次新能源的互聯網式革命?
6月16日,上海的天悶熱難耐,時近中午,氣溫飆升至33攝氏度。黨紀虎的家在松江九亭頤景園,一幢紅色小高層的底樓。此刻他正站在自家6樓的屋頂上,那里溫度直逼40攝氏度,他一邊用抹布擦著由10塊光伏電板拼成的“發電站”,一邊慶幸地說,“照今天這種太陽,發14~15度電應該沒問題!”那些光伏電板在陽光的照耀下,反射著銀亮的光芒。眼前望去,近3萬平米的小區,那些閑置屋頂,仿佛都成了未開墾的“能源森林”。
今年3月,國家電網發布《關于做好分布式電源并網服務工作的意見》,被看作不再對個人光伏發電欲說還休,遮遮掩掩。幾個月過去,和黨紀虎一樣,想將個人發電進行到底的光伏愛好者們,從申請到正式并網,他們的“小小發電站”也已陸續走上正軌。
在近來大熱的暢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作者杰里米·里夫金寫道: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區、經濟公寓、街區、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的工廠,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地產以及工業區繁榮的話,那么,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會將每一個現存的大樓轉變成一個兩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發電廠。
一個人的發電站,這是一次新興能源的互聯網式革命,心動過后,還將迎來什么?
■熱點·成本
4萬元投資十七八年才能收回?
沿著狹長的梯子,記者爬至6樓屋頂,黨紀虎家的樓頂有40多個平米,被兩大塊光伏電板占據后,所剩空間已經不多。“我裝的是2.5千瓦容量,材料、人工、安裝成本等加起來差不多花了4萬元左右!”在他的微博上,記錄著這個迷你電站每天的發電量,數據來源則是他安裝在電腦中的一套監測軟件,隨時可以看到。但也并非“旱澇保收”,發電量多少,全看太陽的心情好壞,“我記得整個2月份,只有2天是晴天,很多時候一天都只發零點幾度電!”盡管如此,從1月安裝使用到5月13日,他的小電站也已兢兢業業地貢獻了1000多度電。更叫黨紀虎興奮的是,3月中旬,他還收到過一張電力公司寄來的電費賬單,不是讓他繳錢,而是給他發錢——196元。這意味著,黨紀虎將用不完的電上傳,賣給了國家電網。
同樣拿到賣電所得的,還有家住閔行的陳繼霖。他的光伏發電站就裝在自家別墅的樓頂,輸出功率也是2.5千瓦,至今收獲的賬單是347元。“解決自家用電基本不成問題,但很多想嘗鮮的人更關心的是,這些投下去的成本什么時候能收回?”陳繼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就算現在是以一元錢一度電的價格賣給國家,日均發電10度,每月300度,算自己用掉一半還剩下150度,4萬元的投資也要十七八年才收得回來,“這個時間實在有點漫長!”
事實上,國家電網公布的《意見》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并網后的補貼標準,而在初期“民間草莽”發展階段,各地多為自行商議補貼方式。以家住北京順義的任凱為例,他目前享受的補貼就和上海不同。他告訴記者,“我們家裝了兩個電表,一個是上傳電表,另一個是自家用電的電表。發電站發的電先統統上傳并給國家電網,而不像上海這邊,自己先用,用不掉的再賣。”而被黨紀虎他們認為不劃算的地方正在于此,自己要用的電,電價總是高于并網回收的價格。但任凱說他知足了,“之前不讓你建,建了也不讓你并網,又能怎么樣呢?現在這樣,保證你能順利發電,順利并網,還給你補貼,已經很OK了。”任凱原先就在一家生產光伏材料的美國公司任職,現在已自己創業,項目就是幫助有“個人光伏發電”意向的人提供設計方案、材料采購、上門安裝等,“手頭上已經有幾個用戶在談了。”
■變化·情勢
從敲68個公章到準“即要即裝”
個人光伏發電的確走過一段曲折的路程。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兩年前,他曾在飯局上碰到某地一位國家電網內部人士,問起為何不準自建發電站并網,對方給出的理由是“不安全”,“但事實上,真實的原因還是國家電網擔心會動了他們的奶酪。”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一度是新聞人物,令他出名的正是家里那座“尷尬”的光伏發電站。2006年,趙春江籌劃建站,從遞交申請材料到最終拿到核準批文,一路敲了68個公章,其中一半以上都來自電力部門。而由于并網政策遲遲不出,趙家的單向電表,無論流進還是流出的電量,都累計用電度數。也就是說,趙春江除了要交正常的電費外,每年還得為自己多生產的電額外上交1000多元錢“發電費”。怎么算,這都是一筆“熱臉貼冷屁股”的虧本賬。
如今,情勢頗叫人感慨“大不同”。原則上,現在上海的申請流程在45個工作日,但陳繼霖從第一次去營業廳咨詢到最后完成安裝驗收只用了20多天。任凱去年10月底申請,今年1月底正式并網驗收,也屬于不慢之列。財經分析人士陳志龍向記者表示,在未來,清潔能源的發展方向一定是好的,在環境屢遭重創、不堪重負之時,環保、無污染的光伏發電,確實會被高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這些第一批的使用者們,更多具有象征意義。”但他同時也認為,他們更像是“票友”,還動搖不了整個的大氣候,“或許在若干年后,仍不足以被稱為新型能源發電的支柱。”但畢竟,被這個新鮮事物吸引、并愿意投身進來的人愈來愈多。上海寶山區的一位用戶,是光伏發電的發燒友,也是一名老師,記者得知,就在他家安裝好發電站后,學生們就盯著他問現在什么大學有類似的新能源專業,很想報考。
■圈內·圈外
粉絲只憑興趣,管它劃不劃算
在個人光伏發電的圈子里,流傳最多的是德國的做法。他們不僅要求電網強制收購居民所發的電數,并且補貼當下電價的2倍。因此放眼望去,德國很多住戶的樓頂上都裝有光伏面板。而陳繼霖甚至還義務設想了很多美好愿景,“郊區不是很多小樓房的屋頂都空著嗎,而且老齡化嚴重,如果變成微型發電站,這對于當地養老也是一樁好事,失去勞動力的老年人也能有收入來源。”
但也有人純粹憑著興趣做事。徐衛雄是崇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至今那里還找不出第二家個人光伏發電站。和其他一些多多少少跟光伏、電力沾點邊的嘗鮮者不同,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圈外粉絲”。“我一直對光伏發電很好奇,去年開始就在網上看資料,去淘寶上找原材料,先看看到底成本要多少,權當作一次實驗吧!”當他發現1.5千瓦的成本在1萬多元后,便決定讓工程上馬。跑了幾趟營業廳,他發現工作人員還沒自己清楚,直到找到縣電力公司的營銷部主任,才算接上頭,也拿到了整套申請流程的PPT。裝好光伏發電站后,抄表員上門過一次,看到徐家的那個電表,懵了,“他說你們家的電表我看不懂,不抄了!”
杰里米·里夫金在書中寫道,“太陽不會一直照耀,風不會一直吹拂,或者即使有風,也可能不是我們需要的那一種。”這也正是徐衛雄小小的煩惱。5月14日下午,他家的小電站正式并網“上崗”,偏偏天氣很不給力,“一個月里20多天是陰雨天,現在又碰上黃梅天,老天在跟我作對哦!”可玩笑歸玩笑,畢竟所發的100多度電,已夠家里電器“開銷”。現在,他自顧自玩得很high,倒是鄰居們替他發愁,“他們幫我算過,說你花了1萬元裝了這么個玩意兒,我們一年用掉1000元電費,能用十年呢。太不劃算了!”不過徐衛雄并不擔心,他說自己就是為了興趣,“我和電力公司的購電合同都還沒簽呢。”
■等待·新政
會有超大力度的補貼嗎?
6月19日上午,記者來到莘北路市南供電營業廳。咨詢窗口聽說記者要申請安裝個人光伏發電站,工作人員拿出《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并網申請表》先請記者看,對方表示,居民需要申請,營業廳都會受理。第一步申請完成后,還需要帶好身份證、房產證、小區物業或居委會或業委會三者中的任意一家出具的同意書,之后才能安裝。
市南供電公司宣傳人士竺士北告訴記者,“畢竟去年底才剛剛開放個人光伏發電,今年3月明確并網要求,所以來咨詢的人不少,但真正接入使用的全上海還只是個位數。”他表示,市民如果是第一次來申請,更多的是雙方坐下來,商定一個最佳方案,“房子結構、物業狀況、安裝事項、用電安全等等,我們都要一一敲定,到安裝完畢后,我們要經過驗收合格,居民才能正式使用。”至于目前補貼1元/度的政策,也是上海本地協商的結果,因為要是依照國家電網的意見,補貼標準是0.477元/度,“各地為了鼓勵大家自建發電,都會有一些變通的做法,但這也只是暫時性的,具體的補貼標準,我們也在等待國家電網的最新通知,一旦標準明確,全國都將采取統一的補貼方式。”
或許你沒有留意的是,在每月收到的電費賬單上,有一項支出是“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收取標準為0.008元/度,“已經收了十年”,任凱說,當然希望這項費用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在這個圈子里,常常流傳一些利好的小道消息。最新的新聞是,江西開始實施萬家屋頂光伏發電示范工程,6月20日起,全省居民均可公開申請。更觸動人心弦的是,他們將撥專項資金補貼居民初裝費,4元/瓦的補貼力度著實叫人羨慕。徐衛雄說,他知道消息后,還馬上發了條短信給之前認識的江西省發改委一個工作人員,“我說上海要是也能有你們這么大力度的補貼就好了!”黨紀虎則羨慕地算起了賬,“2.5千瓦功率就能補貼1萬元,再加上并網后可以賣電,收回成本的時間就會大大縮短。”
6月16日,上海的天悶熱難耐,時近中午,氣溫飆升至33攝氏度。黨紀虎的家在松江九亭頤景園,一幢紅色小高層的底樓。此刻他正站在自家6樓的屋頂上,那里溫度直逼40攝氏度,他一邊用抹布擦著由10塊光伏電板拼成的“發電站”,一邊慶幸地說,“照今天這種太陽,發14~15度電應該沒問題!”那些光伏電板在陽光的照耀下,反射著銀亮的光芒。眼前望去,近3萬平米的小區,那些閑置屋頂,仿佛都成了未開墾的“能源森林”。
今年3月,國家電網發布《關于做好分布式電源并網服務工作的意見》,被看作不再對個人光伏發電欲說還休,遮遮掩掩。幾個月過去,和黨紀虎一樣,想將個人發電進行到底的光伏愛好者們,從申請到正式并網,他們的“小小發電站”也已陸續走上正軌。
在近來大熱的暢銷書《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作者杰里米·里夫金寫道: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區、經濟公寓、街區、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的工廠,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地產以及工業區繁榮的話,那么,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會將每一個現存的大樓轉變成一個兩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發電廠。
一個人的發電站,這是一次新興能源的互聯網式革命,心動過后,還將迎來什么?
■熱點·成本
4萬元投資十七八年才能收回?
沿著狹長的梯子,記者爬至6樓屋頂,黨紀虎家的樓頂有40多個平米,被兩大塊光伏電板占據后,所剩空間已經不多。“我裝的是2.5千瓦容量,材料、人工、安裝成本等加起來差不多花了4萬元左右!”在他的微博上,記錄著這個迷你電站每天的發電量,數據來源則是他安裝在電腦中的一套監測軟件,隨時可以看到。但也并非“旱澇保收”,發電量多少,全看太陽的心情好壞,“我記得整個2月份,只有2天是晴天,很多時候一天都只發零點幾度電!”盡管如此,從1月安裝使用到5月13日,他的小電站也已兢兢業業地貢獻了1000多度電。更叫黨紀虎興奮的是,3月中旬,他還收到過一張電力公司寄來的電費賬單,不是讓他繳錢,而是給他發錢——196元。這意味著,黨紀虎將用不完的電上傳,賣給了國家電網。
同樣拿到賣電所得的,還有家住閔行的陳繼霖。他的光伏發電站就裝在自家別墅的樓頂,輸出功率也是2.5千瓦,至今收獲的賬單是347元。“解決自家用電基本不成問題,但很多想嘗鮮的人更關心的是,這些投下去的成本什么時候能收回?”陳繼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就算現在是以一元錢一度電的價格賣給國家,日均發電10度,每月300度,算自己用掉一半還剩下150度,4萬元的投資也要十七八年才收得回來,“這個時間實在有點漫長!”
事實上,國家電網公布的《意見》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并網后的補貼標準,而在初期“民間草莽”發展階段,各地多為自行商議補貼方式。以家住北京順義的任凱為例,他目前享受的補貼就和上海不同。他告訴記者,“我們家裝了兩個電表,一個是上傳電表,另一個是自家用電的電表。發電站發的電先統統上傳并給國家電網,而不像上海這邊,自己先用,用不掉的再賣。”而被黨紀虎他們認為不劃算的地方正在于此,自己要用的電,電價總是高于并網回收的價格。但任凱說他知足了,“之前不讓你建,建了也不讓你并網,又能怎么樣呢?現在這樣,保證你能順利發電,順利并網,還給你補貼,已經很OK了。”任凱原先就在一家生產光伏材料的美國公司任職,現在已自己創業,項目就是幫助有“個人光伏發電”意向的人提供設計方案、材料采購、上門安裝等,“手頭上已經有幾個用戶在談了。”
■變化·情勢
從敲68個公章到準“即要即裝”
個人光伏發電的確走過一段曲折的路程。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兩年前,他曾在飯局上碰到某地一位國家電網內部人士,問起為何不準自建發電站并網,對方給出的理由是“不安全”,“但事實上,真實的原因還是國家電網擔心會動了他們的奶酪。”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一度是新聞人物,令他出名的正是家里那座“尷尬”的光伏發電站。2006年,趙春江籌劃建站,從遞交申請材料到最終拿到核準批文,一路敲了68個公章,其中一半以上都來自電力部門。而由于并網政策遲遲不出,趙家的單向電表,無論流進還是流出的電量,都累計用電度數。也就是說,趙春江除了要交正常的電費外,每年還得為自己多生產的電額外上交1000多元錢“發電費”。怎么算,這都是一筆“熱臉貼冷屁股”的虧本賬。
如今,情勢頗叫人感慨“大不同”。原則上,現在上海的申請流程在45個工作日,但陳繼霖從第一次去營業廳咨詢到最后完成安裝驗收只用了20多天。任凱去年10月底申請,今年1月底正式并網驗收,也屬于不慢之列。財經分析人士陳志龍向記者表示,在未來,清潔能源的發展方向一定是好的,在環境屢遭重創、不堪重負之時,環保、無污染的光伏發電,確實會被高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這些第一批的使用者們,更多具有象征意義。”但他同時也認為,他們更像是“票友”,還動搖不了整個的大氣候,“或許在若干年后,仍不足以被稱為新型能源發電的支柱。”但畢竟,被這個新鮮事物吸引、并愿意投身進來的人愈來愈多。上海寶山區的一位用戶,是光伏發電的發燒友,也是一名老師,記者得知,就在他家安裝好發電站后,學生們就盯著他問現在什么大學有類似的新能源專業,很想報考。
■圈內·圈外
粉絲只憑興趣,管它劃不劃算
在個人光伏發電的圈子里,流傳最多的是德國的做法。他們不僅要求電網強制收購居民所發的電數,并且補貼當下電價的2倍。因此放眼望去,德國很多住戶的樓頂上都裝有光伏面板。而陳繼霖甚至還義務設想了很多美好愿景,“郊區不是很多小樓房的屋頂都空著嗎,而且老齡化嚴重,如果變成微型發電站,這對于當地養老也是一樁好事,失去勞動力的老年人也能有收入來源。”
但也有人純粹憑著興趣做事。徐衛雄是崇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至今那里還找不出第二家個人光伏發電站。和其他一些多多少少跟光伏、電力沾點邊的嘗鮮者不同,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圈外粉絲”。“我一直對光伏發電很好奇,去年開始就在網上看資料,去淘寶上找原材料,先看看到底成本要多少,權當作一次實驗吧!”當他發現1.5千瓦的成本在1萬多元后,便決定讓工程上馬。跑了幾趟營業廳,他發現工作人員還沒自己清楚,直到找到縣電力公司的營銷部主任,才算接上頭,也拿到了整套申請流程的PPT。裝好光伏發電站后,抄表員上門過一次,看到徐家的那個電表,懵了,“他說你們家的電表我看不懂,不抄了!”
杰里米·里夫金在書中寫道,“太陽不會一直照耀,風不會一直吹拂,或者即使有風,也可能不是我們需要的那一種。”這也正是徐衛雄小小的煩惱。5月14日下午,他家的小電站正式并網“上崗”,偏偏天氣很不給力,“一個月里20多天是陰雨天,現在又碰上黃梅天,老天在跟我作對哦!”可玩笑歸玩笑,畢竟所發的100多度電,已夠家里電器“開銷”。現在,他自顧自玩得很high,倒是鄰居們替他發愁,“他們幫我算過,說你花了1萬元裝了這么個玩意兒,我們一年用掉1000元電費,能用十年呢。太不劃算了!”不過徐衛雄并不擔心,他說自己就是為了興趣,“我和電力公司的購電合同都還沒簽呢。”
■等待·新政
會有超大力度的補貼嗎?
6月19日上午,記者來到莘北路市南供電營業廳。咨詢窗口聽說記者要申請安裝個人光伏發電站,工作人員拿出《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并網申請表》先請記者看,對方表示,居民需要申請,營業廳都會受理。第一步申請完成后,還需要帶好身份證、房產證、小區物業或居委會或業委會三者中的任意一家出具的同意書,之后才能安裝。
市南供電公司宣傳人士竺士北告訴記者,“畢竟去年底才剛剛開放個人光伏發電,今年3月明確并網要求,所以來咨詢的人不少,但真正接入使用的全上海還只是個位數。”他表示,市民如果是第一次來申請,更多的是雙方坐下來,商定一個最佳方案,“房子結構、物業狀況、安裝事項、用電安全等等,我們都要一一敲定,到安裝完畢后,我們要經過驗收合格,居民才能正式使用。”至于目前補貼1元/度的政策,也是上海本地協商的結果,因為要是依照國家電網的意見,補貼標準是0.477元/度,“各地為了鼓勵大家自建發電,都會有一些變通的做法,但這也只是暫時性的,具體的補貼標準,我們也在等待國家電網的最新通知,一旦標準明確,全國都將采取統一的補貼方式。”
或許你沒有留意的是,在每月收到的電費賬單上,有一項支出是“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收取標準為0.008元/度,“已經收了十年”,任凱說,當然希望這項費用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在這個圈子里,常常流傳一些利好的小道消息。最新的新聞是,江西開始實施萬家屋頂光伏發電示范工程,6月20日起,全省居民均可公開申請。更觸動人心弦的是,他們將撥專項資金補貼居民初裝費,4元/瓦的補貼力度著實叫人羨慕。徐衛雄說,他知道消息后,還馬上發了條短信給之前認識的江西省發改委一個工作人員,“我說上海要是也能有你們這么大力度的補貼就好了!”黨紀虎則羨慕地算起了賬,“2.5千瓦功率就能補貼1萬元,再加上并網后可以賣電,收回成本的時間就會大大縮短。”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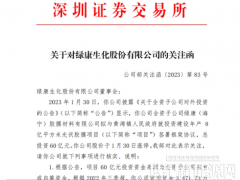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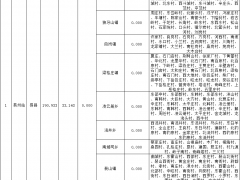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