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改革開放40年同步,我國風電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產業實現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跨越式發展,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成長之路。我國風電發展還面臨哪些困境?未來應如何發展?記者專訪了原中國國電集團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謝長軍,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了發展建議。
記者:回顧改革開放40年,我國風電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
謝長軍:1986年,馬蘭風電場在山東榮成并網發電,裝機容量165千瓦,安裝3臺55千瓦機組。這是全國首座并網發電的風電場,揭開了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建設的大幕。從165千瓦到1.64億千瓦,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前十年,就是試驗研究、示范先行,可以稱為“青銅時代”。這一時期,可再生能源沒有技術基礎,沒有相關政策扶持,也沒有商業化風電場。我國在引進國外風電機組的同時,積極推進自主研制工作,處在風電設備研制的起步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末到2006年,就是商業開發、積累能量,可以稱為“白銀時代”。經過10年蹣跚學步,我國風電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5年,原電力工業部提出到2000年風電裝機達到100萬千瓦的目標,出臺了電網允許風電場就近上網、全額收購風電場上網電量、對高于電網平均電價部分實行全網分攤的鼓勵政策。這是中國第一個風電發展規劃,也是第一個鼓勵發展風電的政策。從1989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風電產業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積累和開發經驗,出現了鼓勵風電發展的政策雛形,出現了商業化開發、公司化運作的嶄新體制。
第三個階段從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實施開始,風電產業進入了大范圍開發、規模發展的“黃金時代”。《可再生能源法》確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明確了政府和社會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加之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收購制度(2009年修訂版完善為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的出臺,對風電產業的崛起和可持續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此后,2006年我國確立可再生能源電費費用分攤制度,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由全社會共同承擔,保證了風電在售電側的平等價格;2008年出臺稅收政策,對風電機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進口關稅實行先征后退,風電企業享受所得稅三免三減半的優惠,進一步優化投資條件;2009年確立分類階梯電價政策,解決了招標電價和審批電價的不確定性問題。
記者:風電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是如何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發展的?
謝長軍:風電場規模化開發建設成為實現風電產業化的關鍵。為此,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啟動風電特許權項目招標,規劃大型風電基地建設。2003年,在第一批風電特許權招標中,華睿投資集團和廣東粵電集團分別中標江蘇如東一期10萬千瓦項目和廣東惠來10萬千瓦項目。但真正打響特許權項目“第一槍”的卻是龍源電力。2004年,在第二批特許權項目招標中,龍源電力以0.519元/千瓦時的價格成功中標江蘇如東(二期)15萬千瓦項目。該項目于2006年10月實現首臺風機并網,2007年底全部投產發電,成為全國投產的首座大型特許權風電項目。
此后幾年,國家相繼啟動多次特許權招標,龍源、華能、國華、中電投、中廣核等公司紛紛參與特許權項目角逐,江蘇如東,吉林通榆,內蒙古巴音、輝騰錫勒,河北承德等多座10萬千瓦以上的大型風電場相繼開建,風電開發逐步由“游擊隊”向“正規軍”轉變。風電場在規模化開發過程中,土地開發、電網架設、配套設施的集約化利用帶來了建設成本的下降,有力推動了大型風電基地的開發建設。風電大規模開發也促進了廣大業主的投資熱情,除了國有大型電力能源企業之外,地方國資企業、各類民營企業和風機制造企業等紛紛進入風電領域,投資風電的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
200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提出在內蒙古、新疆、甘肅、河北、江蘇和吉林建設6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目標,進一步加快風電發展速度,風電產業在短時間內迅速向規模化、產業化發展。2005年,我國風電裝機為127萬千瓦,2006年達到254萬千瓦,2008年突破1000萬千瓦,2009年突破2000萬千瓦,2010年突破4000萬千瓦,先后超越丹麥、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創造了風電發展史上的中國速度。截至2017年底,新疆、甘肅、蒙東、蒙西、河北、山東、寧夏、云南、山西9個地區風電裝機容量超過或接近千萬千瓦。
記者:技術國產化是我國風電發展的必經之路,那么我國風機制造技術經歷了怎樣的探索?
謝長軍: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風機制造技術幾乎是一片空白。1984年,國家計委啟動我國首臺國產風機設計制造,單機容量只有55千瓦。經過10個年頭的漫長技術攻關,1993年4月,我國生產出第一臺國產200千瓦機組。這兩臺試驗機組都在福建平潭并網。到1999年底,我國投運風電機組594臺、26.2萬千瓦,其中國產機組只有29臺、0.84萬千瓦,容量只占全國的3.2%,平均單機容量不到300千瓦,并且這些國產機組并沒有真正大批量生產。進口風機的壟斷,居高不下的機組采購價格,導致中國風電產業化發展舉步維艱。
1999年,新疆風能公司通過引進、消化國外大型風機先進技術,研制出600千瓦風電機組,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并投入達坂城1號風電場運行,主要經濟指標達到國際90年代先進水平,為此后國產化風電機組的規模化生產奠定了基礎。
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進入21世紀,風機設備制造產業終于完成了由風機整機進口到關鍵零部件進口,再到關鍵零部件自主研發的快速升級。2006年以后,曾經在中國風電市場一統天下的國際知名風機制造商,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丹麥的維斯塔斯、西班牙的歌美颯公司、美國的GE公司、西班牙的EHN公司分別在天津、沈陽、南通建廠。同時,華銳、金風、聯合動力、遠景、明陽等一大批本土風機制造企業迅速崛起壯大。2007年新增風電裝機中,國產設備占比已達到55.9%,首次超過外資設備;到了2009年,國產化率已達85%以上,1500千瓦、2000千瓦機組基本實現國產化,取代進口機組成為國內主流機型。
2010年以后,國產陸上2000千瓦以上、海上4000千瓦等多種機型先后問世,并大批量生產投入市場,滿足了中國風電快速增長的需求。在2017年中國新增風電裝機中,本土設備占比超過90%。風機設備國產化進程帶來了機組采購價格的迅速下降,從2006年的6000元/千瓦,下降到今天的3000多元/千瓦,為我國風電規模化發展提供了技術保障。
記者:目前,我國風電發展面臨哪些困境?應如何解決?
謝長軍:一是風電市場出現非理性競爭。由于平價上網的預期,風電開發競爭日趨激烈,2016年和2017年中國風電機組價格連續兩年快速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經降至3200元/千瓦左右。近期一個風電平價上網示范項目招標中甚至出現了3000元/千瓦的投標價格。低價中標模式凸顯出嚴重的弊端,已逐漸引發非理性競爭態勢。今年以來,風機制造行業自上游向下游擠壓的情況逐漸顯現,風機制造的重要原材料鑄鐵從2018年初的3400元/噸漲到11月底的4500元/噸,開發商也不愿輕易讓渡利潤,夾在中游的風機制造企業為了搶占市場,不得不大幅壓縮設備報價。一方面,會助長制造商為拿訂單虛高承諾電量的不正之風,不同企業的2兆瓦機型出現了造價相差300~400元/千瓦、發電量相差1000小時的巨大差別,嚴重扭曲風電開發實際;另一方面風機設備的無節制降價已無法有效向下游傳導,一些零部件供應商選擇退出風機制造領域,還有一些優質產能流向了利潤更高的海外市場,今年已出現塔筒供應緊張的情況。因此,風電場開發建設不能單純以低價為前提,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招標機制,綜合考慮風機價格、機組性能、安全性、市場業績等多個方面,讓有責任心、有創新意愿的制造企業體現出市場價值。
二是限電問題仍然不能掉以輕心。近年來,由于裝機規模的快速增長、電源與電網建設速度不匹配等多重原因,“三北”等地區出現嚴重的限電問題。2016年和2017年全國風電限電量總計約900億千瓦時。2017年3月限電問題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后,電網公司不斷提高重視,嚴格控制接網批復,加之風電投資商放緩發展速度,限電形勢得到了有效緩解,今年前三季度全國風電限電比例下降到7.7%,但限電電量依然高達222億千瓦時,局部地區如新疆(24.6%)、甘肅(19.7%)等棄風形勢仍然較為嚴重。所以,風電仍需堅持理性發展,要與經濟發展、電網建設相適應相匹配,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未來陸上風電每年新增1500~1800萬千瓦為宜。
三是技術創新時間不足恐帶來技術和質量風險。健康的降價之路不應一味通過壓低機組價格來實現,而是依靠技術驅動實現機組發電能力的提升和制造成本的下降。大容量機組技術的研發,高塔筒新材料的應用,生產線的升級革新等,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若強行在2020年推行平價上網,新產品和技術進步的應用和驗證時間明顯不足,會導致整機廠家因為市場生存壓力而降低創新動力和創新投入,只求加快產品上市節奏,放大機組技術和質量風險。事實上,近年來棄風限電的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機組質量和效率問題,高塔筒、長葉片等新技術的應用沒有經過長時間的驗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可能會引發批量性的事故,后果不堪設想。
四是環保問題處理不好將嚴重制約風電產業健康發展。在我國植被覆蓋較好的中、東、南部地區,部分風電場沒有注意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破壞,已有多個省份因此暫停發展風電。現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未來中央政府對項目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將更加嚴格,風電業主將承擔更大的環境風險和法律責任。今年7月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文明確提出要嚴禁風電場項目使用重點林區林地。風電對生態環境的損害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的警覺,如果解決不好,將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
記者: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的大背景下,風電應如何發展?
謝長軍:一是科學有序降低風機造價。設備制造成本要通過新技術研發和應用降下來,不能人為硬壓下來。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機組發電量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設備停機時間和運營成本,最終實現度電成本的下降,這才是實現平價上網的科學途徑。例如,2017年主流機型2.5兆瓦-141、120米高塔筒,與2015年2.0兆瓦-115機型、80米高塔筒相比,由于機組容量、葉片長度、塔筒高度增加等技術創新,在平原高剪切地區發電量可提升15%以上,雖然生產成本也略微上升,但總的結果是風電場度電成本大幅下降。一味壓低風機價格,會削減制造企業技術創新投入,更加無益于降低度電成本。
二是要盡快降低風電非技術成本。要順利實現平價上網,必須降低風電非技術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將風電資源配置給了不具備技術和資金實力的地方性企業,出現倒賣“路條”行為,或者在資源分配時提出收取資源費等訴求;包括前面提到的不能及時落實送出條件造成棄風限電損失。只有消除以上不合規合理的非技術成本,才能還原風電開發真實成本,加快平價上網。
三是平價上網以市場為導向。平價上網是大勢所趨,但是要在2020年完全實現風火同價是不切實際的。要明確一個概念,平價不能完全等同于同價。各地區電量消納能力、資源與造價水平、燃煤標桿電價等條件各不相同,平價上網條件差異很大。新疆、內蒙古(西部)、甘肅是風電大省,但當地燃煤標桿電價分別只有0.26、0.28和0.30元/千瓦時。雖然三個地區資源條件很好,仍不足以支撐風電在這個電價水平生存。因此,要實行因地制宜地平價上網,有條件的省份可率先平價;暫時不具備條件的要隨著技術進步逐步實現平價;對于一些風資源條件一般、燃煤發電電價又很低的省份(如寧夏、山西等),幾年之內都不可能具備同價條件,要允許風電電價略高于火電電價。從明年開始,風電將全面推行競價上網,風電產業進入完全競爭時代。要以市場為導向推進風火平價,不能搞人為地一刀切,預計2020年左右,風電在部分省份實現平價上網;到2022年左右,隨著市場競爭更加充分、深入,才能逐步實現全國大部分地區平價。
四是南北方風電市場要協調平衡發展。限電嚴重的“三北”地區,2020年以前的兩三年將迎來平穩過渡期,預計進入“十四五”以后“三北”地區整體消納環境達到國家預期(限電5%)。2021~2015年,隨著中、東、南部地區土地資源更加有限,風電開發重點將回歸“三北”地區,并贏來新一輪的發展高潮。同時,大葉片機組技術將打破傳統IEC風電場分級標準,通過優化控制策略改善機組載荷,“三北”高風速地區也可以應用大葉片機組,屆時風電項目的經濟效益將更加可觀。南方地區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資源有限、環保等因素,應以發展分散式風電為主。未來,要形成“三北”地區集中式開發、中東南部和內陸低風速地區分散式開發并舉的風電發展格局。
五是切實做好電網規劃。目前棄風限電有所好轉,但面對未來可預期的風電增量,消納壓力依然很大,進一步提升送出能力才是解決限電問題的根本之道。特別是明年將開啟風電競價上網,今年年內核準的一批存量保價項目將在未來1~2年內得到產能釋放。若電網建設不能明確規劃,不能匹配風電場建設速度,限電形勢很可能會出現反彈。電網企業要明確具體的規劃時間表,加快建設步伐,使電網與電源建設規劃相匹配。今年9月,國家能源局下發《關于加快推進一批輸變電重點工程規劃建設工作的通知》,將在今明兩年核準9個重點輸變電工程,包括12條特高壓線路。要確保這些送出線路按規劃時間投產,為未來風電消納提供保障。
記者:回顧改革開放40年,我國風電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
謝長軍:1986年,馬蘭風電場在山東榮成并網發電,裝機容量165千瓦,安裝3臺55千瓦機組。這是全國首座并網發電的風電場,揭開了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建設的大幕。從165千瓦到1.64億千瓦,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前十年,就是試驗研究、示范先行,可以稱為“青銅時代”。這一時期,可再生能源沒有技術基礎,沒有相關政策扶持,也沒有商業化風電場。我國在引進國外風電機組的同時,積極推進自主研制工作,處在風電設備研制的起步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末到2006年,就是商業開發、積累能量,可以稱為“白銀時代”。經過10年蹣跚學步,我國風電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5年,原電力工業部提出到2000年風電裝機達到100萬千瓦的目標,出臺了電網允許風電場就近上網、全額收購風電場上網電量、對高于電網平均電價部分實行全網分攤的鼓勵政策。這是中國第一個風電發展規劃,也是第一個鼓勵發展風電的政策。從1989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風電產業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積累和開發經驗,出現了鼓勵風電發展的政策雛形,出現了商業化開發、公司化運作的嶄新體制。
第三個階段從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實施開始,風電產業進入了大范圍開發、規模發展的“黃金時代”。《可再生能源法》確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明確了政府和社會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加之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收購制度(2009年修訂版完善為全額保障性收購制度)的出臺,對風電產業的崛起和可持續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此后,2006年我國確立可再生能源電費費用分攤制度,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由全社會共同承擔,保證了風電在售電側的平等價格;2008年出臺稅收政策,對風電機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進口關稅實行先征后退,風電企業享受所得稅三免三減半的優惠,進一步優化投資條件;2009年確立分類階梯電價政策,解決了招標電價和審批電價的不確定性問題。
記者:風電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是如何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發展的?
謝長軍:風電場規模化開發建設成為實現風電產業化的關鍵。為此,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啟動風電特許權項目招標,規劃大型風電基地建設。2003年,在第一批風電特許權招標中,華睿投資集團和廣東粵電集團分別中標江蘇如東一期10萬千瓦項目和廣東惠來10萬千瓦項目。但真正打響特許權項目“第一槍”的卻是龍源電力。2004年,在第二批特許權項目招標中,龍源電力以0.519元/千瓦時的價格成功中標江蘇如東(二期)15萬千瓦項目。該項目于2006年10月實現首臺風機并網,2007年底全部投產發電,成為全國投產的首座大型特許權風電項目。
此后幾年,國家相繼啟動多次特許權招標,龍源、華能、國華、中電投、中廣核等公司紛紛參與特許權項目角逐,江蘇如東,吉林通榆,內蒙古巴音、輝騰錫勒,河北承德等多座10萬千瓦以上的大型風電場相繼開建,風電開發逐步由“游擊隊”向“正規軍”轉變。風電場在規模化開發過程中,土地開發、電網架設、配套設施的集約化利用帶來了建設成本的下降,有力推動了大型風電基地的開發建設。風電大規模開發也促進了廣大業主的投資熱情,除了國有大型電力能源企業之外,地方國資企業、各類民營企業和風機制造企業等紛紛進入風電領域,投資風電的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
200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提出在內蒙古、新疆、甘肅、河北、江蘇和吉林建設6個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的目標,進一步加快風電發展速度,風電產業在短時間內迅速向規模化、產業化發展。2005年,我國風電裝機為127萬千瓦,2006年達到254萬千瓦,2008年突破1000萬千瓦,2009年突破2000萬千瓦,2010年突破4000萬千瓦,先后超越丹麥、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創造了風電發展史上的中國速度。截至2017年底,新疆、甘肅、蒙東、蒙西、河北、山東、寧夏、云南、山西9個地區風電裝機容量超過或接近千萬千瓦。
記者:技術國產化是我國風電發展的必經之路,那么我國風機制造技術經歷了怎樣的探索?
謝長軍: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風機制造技術幾乎是一片空白。1984年,國家計委啟動我國首臺國產風機設計制造,單機容量只有55千瓦。經過10個年頭的漫長技術攻關,1993年4月,我國生產出第一臺國產200千瓦機組。這兩臺試驗機組都在福建平潭并網。到1999年底,我國投運風電機組594臺、26.2萬千瓦,其中國產機組只有29臺、0.84萬千瓦,容量只占全國的3.2%,平均單機容量不到300千瓦,并且這些國產機組并沒有真正大批量生產。進口風機的壟斷,居高不下的機組采購價格,導致中國風電產業化發展舉步維艱。
1999年,新疆風能公司通過引進、消化國外大型風機先進技術,研制出600千瓦風電機組,國產化率達到90%以上,并投入達坂城1號風電場運行,主要經濟指標達到國際90年代先進水平,為此后國產化風電機組的規模化生產奠定了基礎。
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進入21世紀,風機設備制造產業終于完成了由風機整機進口到關鍵零部件進口,再到關鍵零部件自主研發的快速升級。2006年以后,曾經在中國風電市場一統天下的國際知名風機制造商,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丹麥的維斯塔斯、西班牙的歌美颯公司、美國的GE公司、西班牙的EHN公司分別在天津、沈陽、南通建廠。同時,華銳、金風、聯合動力、遠景、明陽等一大批本土風機制造企業迅速崛起壯大。2007年新增風電裝機中,國產設備占比已達到55.9%,首次超過外資設備;到了2009年,國產化率已達85%以上,1500千瓦、2000千瓦機組基本實現國產化,取代進口機組成為國內主流機型。
2010年以后,國產陸上2000千瓦以上、海上4000千瓦等多種機型先后問世,并大批量生產投入市場,滿足了中國風電快速增長的需求。在2017年中國新增風電裝機中,本土設備占比超過90%。風機設備國產化進程帶來了機組采購價格的迅速下降,從2006年的6000元/千瓦,下降到今天的3000多元/千瓦,為我國風電規模化發展提供了技術保障。
記者:目前,我國風電發展面臨哪些困境?應如何解決?
謝長軍:一是風電市場出現非理性競爭。由于平價上網的預期,風電開發競爭日趨激烈,2016年和2017年中國風電機組價格連續兩年快速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經降至3200元/千瓦左右。近期一個風電平價上網示范項目招標中甚至出現了3000元/千瓦的投標價格。低價中標模式凸顯出嚴重的弊端,已逐漸引發非理性競爭態勢。今年以來,風機制造行業自上游向下游擠壓的情況逐漸顯現,風機制造的重要原材料鑄鐵從2018年初的3400元/噸漲到11月底的4500元/噸,開發商也不愿輕易讓渡利潤,夾在中游的風機制造企業為了搶占市場,不得不大幅壓縮設備報價。一方面,會助長制造商為拿訂單虛高承諾電量的不正之風,不同企業的2兆瓦機型出現了造價相差300~400元/千瓦、發電量相差1000小時的巨大差別,嚴重扭曲風電開發實際;另一方面風機設備的無節制降價已無法有效向下游傳導,一些零部件供應商選擇退出風機制造領域,還有一些優質產能流向了利潤更高的海外市場,今年已出現塔筒供應緊張的情況。因此,風電場開發建設不能單純以低價為前提,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招標機制,綜合考慮風機價格、機組性能、安全性、市場業績等多個方面,讓有責任心、有創新意愿的制造企業體現出市場價值。
二是限電問題仍然不能掉以輕心。近年來,由于裝機規模的快速增長、電源與電網建設速度不匹配等多重原因,“三北”等地區出現嚴重的限電問題。2016年和2017年全國風電限電量總計約900億千瓦時。2017年3月限電問題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后,電網公司不斷提高重視,嚴格控制接網批復,加之風電投資商放緩發展速度,限電形勢得到了有效緩解,今年前三季度全國風電限電比例下降到7.7%,但限電電量依然高達222億千瓦時,局部地區如新疆(24.6%)、甘肅(19.7%)等棄風形勢仍然較為嚴重。所以,風電仍需堅持理性發展,要與經濟發展、電網建設相適應相匹配,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未來陸上風電每年新增1500~1800萬千瓦為宜。
三是技術創新時間不足恐帶來技術和質量風險。健康的降價之路不應一味通過壓低機組價格來實現,而是依靠技術驅動實現機組發電能力的提升和制造成本的下降。大容量機組技術的研發,高塔筒新材料的應用,生產線的升級革新等,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若強行在2020年推行平價上網,新產品和技術進步的應用和驗證時間明顯不足,會導致整機廠家因為市場生存壓力而降低創新動力和創新投入,只求加快產品上市節奏,放大機組技術和質量風險。事實上,近年來棄風限電的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機組質量和效率問題,高塔筒、長葉片等新技術的應用沒有經過長時間的驗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可能會引發批量性的事故,后果不堪設想。
四是環保問題處理不好將嚴重制約風電產業健康發展。在我國植被覆蓋較好的中、東、南部地區,部分風電場沒有注意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破壞,已有多個省份因此暫停發展風電。現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未來中央政府對項目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將更加嚴格,風電業主將承擔更大的環境風險和法律責任。今年7月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文明確提出要嚴禁風電場項目使用重點林區林地。風電對生態環境的損害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的警覺,如果解決不好,將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
記者: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的大背景下,風電應如何發展?
謝長軍:一是科學有序降低風機造價。設備制造成本要通過新技術研發和應用降下來,不能人為硬壓下來。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機組發電量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設備停機時間和運營成本,最終實現度電成本的下降,這才是實現平價上網的科學途徑。例如,2017年主流機型2.5兆瓦-141、120米高塔筒,與2015年2.0兆瓦-115機型、80米高塔筒相比,由于機組容量、葉片長度、塔筒高度增加等技術創新,在平原高剪切地區發電量可提升15%以上,雖然生產成本也略微上升,但總的結果是風電場度電成本大幅下降。一味壓低風機價格,會削減制造企業技術創新投入,更加無益于降低度電成本。
二是要盡快降低風電非技術成本。要順利實現平價上網,必須降低風電非技術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將風電資源配置給了不具備技術和資金實力的地方性企業,出現倒賣“路條”行為,或者在資源分配時提出收取資源費等訴求;包括前面提到的不能及時落實送出條件造成棄風限電損失。只有消除以上不合規合理的非技術成本,才能還原風電開發真實成本,加快平價上網。
三是平價上網以市場為導向。平價上網是大勢所趨,但是要在2020年完全實現風火同價是不切實際的。要明確一個概念,平價不能完全等同于同價。各地區電量消納能力、資源與造價水平、燃煤標桿電價等條件各不相同,平價上網條件差異很大。新疆、內蒙古(西部)、甘肅是風電大省,但當地燃煤標桿電價分別只有0.26、0.28和0.30元/千瓦時。雖然三個地區資源條件很好,仍不足以支撐風電在這個電價水平生存。因此,要實行因地制宜地平價上網,有條件的省份可率先平價;暫時不具備條件的要隨著技術進步逐步實現平價;對于一些風資源條件一般、燃煤發電電價又很低的省份(如寧夏、山西等),幾年之內都不可能具備同價條件,要允許風電電價略高于火電電價。從明年開始,風電將全面推行競價上網,風電產業進入完全競爭時代。要以市場為導向推進風火平價,不能搞人為地一刀切,預計2020年左右,風電在部分省份實現平價上網;到2022年左右,隨著市場競爭更加充分、深入,才能逐步實現全國大部分地區平價。
四是南北方風電市場要協調平衡發展。限電嚴重的“三北”地區,2020年以前的兩三年將迎來平穩過渡期,預計進入“十四五”以后“三北”地區整體消納環境達到國家預期(限電5%)。2021~2015年,隨著中、東、南部地區土地資源更加有限,風電開發重點將回歸“三北”地區,并贏來新一輪的發展高潮。同時,大葉片機組技術將打破傳統IEC風電場分級標準,通過優化控制策略改善機組載荷,“三北”高風速地區也可以應用大葉片機組,屆時風電項目的經濟效益將更加可觀。南方地區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資源有限、環保等因素,應以發展分散式風電為主。未來,要形成“三北”地區集中式開發、中東南部和內陸低風速地區分散式開發并舉的風電發展格局。
五是切實做好電網規劃。目前棄風限電有所好轉,但面對未來可預期的風電增量,消納壓力依然很大,進一步提升送出能力才是解決限電問題的根本之道。特別是明年將開啟風電競價上網,今年年內核準的一批存量保價項目將在未來1~2年內得到產能釋放。若電網建設不能明確規劃,不能匹配風電場建設速度,限電形勢很可能會出現反彈。電網企業要明確具體的規劃時間表,加快建設步伐,使電網與電源建設規劃相匹配。今年9月,國家能源局下發《關于加快推進一批輸變電重點工程規劃建設工作的通知》,將在今明兩年核準9個重點輸變電工程,包括12條特高壓線路。要確保這些送出線路按規劃時間投產,為未來風電消納提供保障。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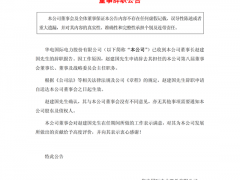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