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至今光伏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上最炫目的風景之一。
比如據黑鷹光伏團隊統計,截至6月30日,光伏上市公司總市值為7262.10億元,較年初增加了1585.78億元,增幅為27.94%;又比如8月21日隆基、通威、陽光電源、東方日升等至少7家光伏公司紛紛漲停,其與光伏上市公司股價也近乎全線飄紅;8月28日隆基更是一舉突破千億市值大關。市場普遍認為,引發此次光伏資本紅色浪潮的根由是“光伏旺季即將來臨”。
2019年光伏企業無論在產業端還是資本端的布局確實也都給人一種很兇猛的感覺。比如據黑鷹光伏團隊統計:2019上半年,數十家光伏企業公布了超千億的產業擴張方案,其中單個項目超十億元的重大投資項目就多達27個,擴張領域不僅覆蓋光伏全產業鏈,甚至延伸至風電、水電、半導體等領域;另外2019年上半年至少有35家光伏企業公布了融資方案/計劃,它們計劃融資額近1400億元。
但是,我們縱觀光伏近二十年發展史,光伏產業經歷了幾輪擴張潮,而每次擴張潮都以某個巨頭的倒下而結束,其產生的破壞力甚至將持續數年。當下需要警惕的是,一系列數據證明光伏產業的風險及壓力也在加速聚集:
一方面,201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就超過1400億元,補貼資金缺口巨大及撥放不及時,已嚴重制約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影響電站投資商的生存與發展。由于光伏電站投資運營商巨額應收款難以快速變現,只能將資金壓力及風險向產業鏈上游層層傳遞,如今巨大的應收款壓力已籠罩整個光伏產業。黑鷹光伏統計發現,截至2018年末,78家主要光伏公司應收賬款及票據規模為1717.67億元,約是它們2018年所創造凈利潤的8.03倍。
這個壓力還在不斷向下傳遞,數據顯示,2018年這78家光伏公司在“應收賬款及票據”規模同比下降的2.45%的情況下,其“應付賬款及票據”規模卻同比增長了6.54%,這或許意味著更多的企業將資金壓力及風險轉移到了中小供應商的身上。
另一方面光伏整體融資環境更是不容樂觀,比如2018年光伏上市公司整體凈籌資現金流僅為157.4億元,較2017年巨降了700.64億元;前十名光伏上市公司凈融資現金流合計為282.54億元,占整體比重達179.50%。如今很多中小企業不僅面臨后續融資難的問題,甚至已經遭遇了“抽貸”的現象,資金壓力已經嚴重影響這些企業生存。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風險和壓力應引起企業的高度重視。截至目前56家光伏企業擔保總額高達約1308.5億元,前30名企業擔保總額都在10億元以上。部分企業已經爆出了擔保危機,企業面臨巨額補償,甚至破產重整危機(詳見下文)。
再回到公司層面,在應收賬款回款難、融資形勢嚴峻等綜合因素下,很多企業都面臨著巨大的短期償債壓力,部分老牌巨頭諸如興業太陽能、海潤光伏等都發生了債務逾期,甚至部分企業被列入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它們面臨著控制權轉讓、退市、破產重組等命運。
為了讓讀者對這些危機及風險有更直接、深刻的認知,我們挑選了10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它們的跌宕興衰,在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進程里代表了不同的企業發展樣本,具有極高的借鑒意義,其中況味,諸君意會。
特別要鄭重聲明的是:黑鷹此次分析這些光伏企業沒有任何嘲諷之意,十年來光伏行業來來去去,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不勝枚舉,很多企業即便一時“失敗”、或陷入困境之中,但其對中國光伏的發展也貢獻了一份力量。黑鷹復盤這些企業是通過分析其“因何而敗”,為讀者提供一個思考的維度,希望引以為戒,這便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初心。
1.昱輝陽光
作為老牌的光伏企業之一,李仙壽創立的浙江昱輝陽光能源有限公司曾頗有名氣。但從去年至今,這家光伏企業顯然陷入了經營困境。
2001年,在開創昱輝陽光之前,李仙壽建立了玉環太陽能能源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商業和住宅用太陽能電池和組件產品制造企業。4年之后,李仙壽才和另外三個伙伴在浙江嘉善姚莊,正式創立了昱輝陽光。或許他們自己都沒想到,這個最初只有150萬美元注冊資本的小公司,日后會創造怎樣的輝煌。可能更沒有想到輝煌過后的折騰與跌宕。
2019年7月8日,浙江昱輝陽光能源有限公司(美股代碼SOL)發布公告稱,李仙壽先生辭去CEO職務(包括在子公司擔任的管理職務),公司同時任命Shelley Xu女士作為新任CEO。公告稱,這位歷經產業跌宕的企業家辭職是由于是“個人原因”。
緊接著,有媒體從全國法院執行信息平臺獲悉,昱輝陽光于7月22日4次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老板李仙壽已被限制消費,執行法院是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昱輝陽光的經營業績到底如何?李仙壽曾表示,未來昱輝陽光要以全球輕資產項目開發模式為戰略,重點關注分布式發電和屋頂太陽能。眾所周知的是,昱輝陽光已于2017年底徹底退出了太陽能組件制造業務。
不過,對于這家企業的轉型與復興,如果系統梳理企業多年來的經營數據,一言以蔽之:壓力重重。
以昱輝陽光2019第一季度的財報為例:營收1310萬美元,環比增長134%,同比下降71%;所得稅和非控制性權益前的虧損為550萬美元;毛利潤40萬美元,環比下降86.2%,同比下降95.2%,毛利率僅為2.8%。目前,昱輝陽光約有1.4吉瓦的太陽能發電項目,其中擁有227.5兆瓦的在運營屋頂項目。
從更長的時間周期來分析,也許我們可以對這家企業面臨的處境看得更加清楚,黑鷹光伏曾梳理昱輝陽光上市至今的部分核心經營數據,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家老牌光伏企業確實陷入了經營困境:





2.興業太陽能
531新政公布以后,有著15年歷史的興業太陽能(0750.HK)成為第一個債務暴雷的光伏上市企業。10月17日,興業太陽能公告稱,其1.6億美元優先票據(年息6.75%)未能如期償付,造成付款違約并觸發另2.6億美元優先票據和9.3億人民幣可轉債的交叉違約。
事實上,在興業太陽能債務暴雷前夕其還發布了一份頗為亮麗的半年報:2018上半年營業收入達30.24億元,同比增長了3.87%,凈利潤為2.28億元,同比增幅185.67%,毛利率也較上一年同期增長3.57%至24.40%;另外其資產負債率也下降了3.01%。
興業太陽能爆發債務危機,主要在于其對現金流掌控力不足。筆者在審閱興業太陽能2018年上半年財報中“現金流量表”及“資產負債表”時發就現諸多有違財務邏輯的地方。
比如在興業太陽能營業收入、凈利潤上半年分別同比增加1.12億元、1.49億元的情況下,其經營現金流凈額卻同比減少了6.20億元至-2.16億元。也就是說,上半年興業太陽能營收、凈利潤雖然看似增長不少,但其并沒有收到真金白銀。
更為嚴峻的是,上半年興業太陽能“籌資現金流”僅為1.04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2.87億元。這是為何?
“經營現金流”、“籌資現金流”一個代表企業自身“造血能力”,一個彰顯企業“融資能力”,興業太陽能兩項能力的巨幅下滑,直接導致了上半年“現金凈增加額”減少了17.26億元。
而看似興業太陽能上半年資產負債率下降了3.01%。但其“短期借款及長期借貸到期部分”增加了14.32億元至42.11億元,這創出了自2009年上市以來19個財報(包括年報及半年報)歷史新高。而截至2018年6月末,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為13.96億元(同比減少了10.64億元)。
“若再加上2019年到期未贖回的人民幣9.6千萬的可轉債,公司的總違約債務約為人民幣30 億。在計入2018 年6月末時的人民幣32.6億銀行貸款后,公司的總債務約達人民幣63億。當前凈債務預計約為人民幣46億。”國泰君安如是說。
如上所述,興業太陽能此次爆發債務危機除了對企業現金流“失控”之外,還與管理層過于樂觀的態度以及缺乏消減負債率的決心及掌控力有直接關系。
早在2016年中期業績說明會上,興業太陽能財務總監余俊敏表示,上半年興業太陽能負債比率為68.8%,集團目標將負債率減至50%以下水平,但進度就要視集團賣電站的進展而定,將優先出售位于西北的電站。
但事實卻是,自2014年至今,興業太陽能資產負債率從未低于60%。而且,即便在2018年半年財報中興業太陽能仍舊表示,“本集團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自建筑合同及材料銷售的應收款項,以及來自電力銷售的收入。”憑借現有現金資源以及從銀行獲取的信貸,本集團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來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事實卻是,在興業太陽能發布2018年半年財報26天后,其就爆發了債務危機。
同時,數據顯示興業太陽能也面臨著巨大的應收賬款回款壓力。如表所示,興業太陽能應收賬款及票據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已經連續6年增長,2018年末已經達到75.73%。財報還顯示:截至2018年6月末,興業太陽能“已逾期”應收貿易款及應收票據規模為11.07億元,同比增加了3054萬元,同比增長了2.84%。一些列數據多少說明了興業太陽能對“應收賬款”似乎逐漸失去了掌控力,這也為其債務危機買下了隱患。
2018年財報顯示:2018年興業太陽能營業收入下降了23.56%至44.75億元,虧損了6.79億元,同比下降了572.05%。
1月22日晚間,興業太陽能發布公告稱, 公司第一大股東Strong Eagle與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山東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訂了了諒解備忘錄,水發能源集團將擁有不少于公司發行股份之50.1%。8月26日上午,雙方聯合召開股權并購重組工作說明會,向珠海市政府相關部門及銀行債委會匯報了并購重組工作的最新進展。雙方計劃在10月底前完成交割。
3.海潤光伏
成立于2004年的海潤光伏曾是中國最大的晶硅太陽能電池生產企業之一,公司在國內江蘇、安徽、云南三省擁有六大生產基地,員工總數超過6000人,晶體硅一體化產能位居全球前十。
據黑鷹光伏統計,最兇猛時,曾在一年之內成立(計劃)64家公司,在全國內跑馬圈地;5年計劃投建光伏電站規模合計約為16GW,粗略統計計劃投資總額高達1600億元,彼時的海潤意氣風發,劍指“獅子王”寶座,力圖成為“千億級市值企業”。
然而,現實卻是2012年-2018年7年間海潤扣非后連續虧損,累計虧損達75.16億元,其在2019年7月12日更是以“退市”落幕。
筆者分析認為,海潤之敗在于當時(2011年)對國內外局勢預測過于樂觀,與后勢有嚴重偏差。海潤逆勢進擊、過早布局國內下游電站領域,為后來的敗北埋下了重大隱患;而海潤之敗根本原因還在于其羸弱的資本實力,與帝國野心存在巨大鴻溝。
數據顯示,自2011年-2017年前三季度,海潤凈籌資現金流僅為73.29億元,經營現金流僅為17.32億元,兩者合計也不過90.61億元,僅為上述計劃投資額的5.66%。打仗打的就是錢糧,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持,再好的策略也不過紙上談兵。
據最新財報,截至2019年3月末,海潤光伏“貨幣資金”儲備僅為1.01億元,“短期借款”規模為9.43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規模為13.63億元,其資金壓力可想而知。
另據黑鷹光伏統計,至今海潤光伏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法律案件”共計102件,最早立案時間為2017年8月17日,最近一次立案時間為2019年6月24日,這些訴訟案件累計“執行標的/未履行金額”合計高達384593萬元。
4.英利
英利綠色能源成立于1998年,生于河北保定,公司產品和服務涵蓋了從多晶硅鑄錠、硅片、光伏電池片、光伏電池組件的生產到系統安裝的整個光伏產業鏈。
在苗連生領導下的英利曾被業內視為“價格屠夫”,2007年英利綠色能源在苗連生掌舵下,成功搶灘美國紐交所,市值達22.66億美元,在10家海外上市的中國光伏企業中位列第三。這一年,51歲的苗連生以137.6億元身價躋身《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成為“河北首富”。
2010年,英利還贊助了南非世界杯,成為首家贊助世界杯的中國企業,彼時英利風頭一時無兩,時隔4年后,英利2014年再次贊助了巴西世界杯。
據黑鷹光伏統計,在2007-2016年這十年間,英利綠色能源實現營業收入合計達1021億元,但是,公司自2011年以來卻深陷虧損泥潭難以自拔,6年里公司累計虧損172.16億元,十年累計虧損153.05億元。
這期間英利還爆發了債務危機,比如2015年10月英利子公司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筆超10億元的債務未能按期足額兌付;2016年5月,天威英利發行總額14億元的債券也宣告違約。期間,在銀保監會的指導下,國家開發銀行率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多家債權銀行組建了英利集團金融債權人委員會,涉及金融債務達到120億元。
2018年6月,英利因“未能在連續30個交易日內保持至少5000萬美元的平均全球市值,且其股東權益不足5000萬美元,不符合持續上市標準”,被紐交所暫停ADS交易。
知名行業專家紅煒老師曾評論道:“2011年以后,英利在光伏加工環節和電站環節連續發力,先是2012、2013年成為全球組件出貨量第一,后是2013年宣布5年時間建成13-15GW光伏電站、進入國內光伏電站建設前兩名,勢必造成負債率過高、資金緊張。”
2019年7月8日英利官網發表了一篇《英利老苗有話說》,在文中苗連生坦言,“這幾年,英利遇到了天大的困難,過得實在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今天就不說這個了。”在此文中,老苗主要是為了表示“感謝”——“感謝黨中央國務院對英利的高度重視和這么強有力的支持!”最后老苗說,黨中央國務院這么關懷民營實體經濟,作為光伏行業咱們就剩下一個字了,干!為責任干,為擔當干。
根據《證券日報》在2019年6月初報道,近日,在國家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光伏企業英利綠色能源歷經3年,債務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據多方了解,其框架性重組方案已形成,并完成向相關部門和國務院報告,將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重組完成后,英利將成為國有控股的企業。
5.順風清潔能源
順風清潔能源早年因以黑馬姿態將破產重組的無錫尚德收入賬下,而名震光伏江湖。在2013年11月順風清潔能源將無錫尚德收入賬下之時,無錫尚德經確認的債權金額便高達107億元。
在有著“光伏圈并購帝”之稱鄭建明帶領下順風清潔能源此后還拿下了德國光伏企業S.A.G、美國光伏制造商Suniva以及LED企業晶能光電。
利潤表顯示,瘋狂的并購雖然讓順風清潔能源營業收入從2012年的10.69億元暴增至2018年的103.27億元,短短六年間暴漲了8.66倍,但是其“扣非后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僅在2014年盈利8906萬元,2015年-2018年合計虧損了558172萬元。
造成這樣的“兩極現象”主要是因為順風清潔能源一系列并購資金主要來自于外部債務融資,據黑鷹光伏統計,順風清潔能源6年間“短期借款”已經從2012年末的90322萬元增長至2018年末的714808萬元,6年時間增長了6.91倍。另外截至2018年末其“長期借款”也增長至391926萬元,其資產負債率已經達到了創歷史新高的85.64%。而截至2018末,順風清潔能源“貨幣資金”僅為75459萬元。
在舉債擴張的策略下,順風清潔能源“利息支出”從2012年的7473萬元增長至2018年的128592萬元,增長了16.21倍,高居不下的利息費已經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在利潤端及資產端均承受重壓的順風清潔能源市值遭遇“雪崩”:五年前(2014年)順風清潔能源市值一度達到260億港元,可如今(2019年8月27日)其市值僅為10.71億港元,巨降了95.88%。
2019年3月,順風光電公告顯示,擬以30億元價格出售旗下江蘇順風光電100%股權,而無錫尚德正是順風光電體系之內。
如今尚德的形勢仍不容樂觀。據黑鷹光伏調查統計,截至目前無錫尚德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涉及“法律案件”共計4件,最早立案時間為2018年5月3日,最近一次立案時間為2019年6月19日,這些訴訟案件累計“執行標的”合計達23517萬元。
6.大海集團
時間回撥到2018年11月26日,山東大海集團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據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大海集團)擔保企業出現問題等一系列因素導致大海集團資不抵債,走上破產重組的道路。”《山東大海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債券2017年年度報告(修訂版)》補充公告顯示,截至2017年末,大海集團為14家企業擔保,對外擔保合計204665萬元。
擔保可以說是民營企業貸款等融資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家遭遇擔保危機的企業老總對中國經濟周刊解釋說:“企業向銀行貸款,可以采取抵押貸款的形式,但局限于抵押物(如土地、設備等)的價值,貸款額度通常較小,難以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如果有其他企業為它做擔保,額度就會擴大,甚至超過抵押貸款額度的10倍以上。通過擔保,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度大大下降,而一旦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為其作保的企業就要履行代償義務。”
需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是,大海集團遭遇的擔保危機并非光伏行業個例。據黑鷹光伏統計,2018年順風清潔能源、航天機電所擔保企業或宣布破產、或債務逾期,順風清潔能源、航天機電需承擔相應的償付責任,金額分別約為26420萬元和2354萬元。
1月21日,向日葵也發布了其擔保的浙江榮盛紡織有限公司等被擔保單位破產清算進展情況,根據《民事裁定書及和解協議》,向日葵對該事項預計計提擔保損失 4757萬元。
而黑鷹光伏統計,截至目前56家光伏企業擔保總額高達約1308.5億元,前30名企業擔保總額都在10億元以上。
目前出現擔保危機的光伏企業都來自于外部擔保風險(對外部企業擔保)。據黑鷹光伏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末約有22家光伏企業對外部企業提供擔保規模為150.31億元(不包括對子公司擔保)。前四名企業對外擔保規模都在十億元以上。
7.科林環保
科林環保原來是家工業粉塵治理解決方案提供商,是國內最大的袋式除塵設備專業制造企業之一,自2016年底開始轉型為光伏電站開發及運營商,2018年其光伏業務實現收入8256萬元,虧損53851萬元,分別同比下降了90.68%和1394.23%。
在“受宏觀經濟及金融政策影響,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年內到期的融資大多未能續貸甚至被抽貸,償還該等融資擠占了公司大量流動資金。”甚至出現部分債務逾期的現象(公司及子公司累計逾期債務合計金額約13288萬元)。
7月13日,科林環保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19年上半年虧損1900萬元-2400萬元(去年同期盈利2819萬元)。
“公司前期已墊資修建的光伏電站未能如期收回墊資款,造成公司運營資金緊缺,同時,受光伏政策以及流動性緊張等因素的影響,較大程度制約了公司光伏電站相關項目的開發、建設規模,從而影響了整體銷售收入、凈利潤的增長,而運營管理費用、折舊攤銷、利息支出等各項剛性支出并未隨之減少,影響本期凈利潤。”科林環保如此解釋道。
黑鷹光伏發現,7月中旬科林環保及實際控制人黎東先生被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并被出具了《限制消費令》。
截至8月16日,科林環保及全資子公司連續十二個月內累計訴訟(在訴)金額合計為 18058萬元,占公司2018年凈資產的90.33%。
財報顯示,截至2019年3月末,科林環保“貨幣資金”僅為5880萬元,其“短期借款”規模為7500萬元,長期借款為9256萬元,其形勢不容樂觀。
作為上市公司科林環保尚且面臨如此境況,其他中小光伏電站開發商又如何呢?
8.中利集團
2011年,中利集團通過并購手段逆勢搏擊光伏行業,當時有人質疑說它“買了個爛攤子”、“逆市進入光伏業接盤嫌疑大”,但中利集團用6年時間硬生生又在光伏領域打造了一艘“百億級”戰艦。
在531新政頒布后,中利集團比較樂觀認為“光伏扶貧電站業務的拓展規避了531光伏新政對公司的不利影響,公司按照既定目標,持續加大光伏扶貧電站業務開發力度,其已成為公司利潤的重要來源。”
在王柏興眼中“光伏扶貧”是其光伏戰略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光伏扶貧確實很難賺錢。但是根據國家扶貧辦估算,每年光伏扶貧的安裝量不會少于2GW。如果中利的光伏扶貧規模真的能上去,我就能把我的組件賣出去。”
然而事實證明,中利集團管理層對扶貧市場的預期似乎過于樂觀了。
要知道早在2018年3月26日,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發布的《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指出,光伏扶貧電站不得負債建設,企業不得投資入股,這使得在資金來源上,光伏扶貧項目只能用政府性資金包括各級財政資金、定點幫扶和社會捐贈資金。
而據黑鷹光伏了解,中利光伏扶貧產業基金為村級光伏扶貧項目提供的是“借入”資金,這個政策對中利光伏扶貧戰略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2018年全年中利集團“由于受光伏扶貧326政策影響,扶貧光伏電站開工數量490MW比預期下降51%。”2018年度中利集團實現營業收入167.26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3.85%。歸屬于母公司凈利潤為-2.88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4.25%。
2019年上半年中利集團營業收入再度同比下降了22.29%至57.35億元;歸屬于母公司凈利潤為1302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73.60%。其中其光伏收入合計為24.18億元,同比下降了38.76%,如下表所示“扶貧電站收入”降幅最大,另外其“光伏組件及電池片”、“光伏電站”收入降幅也都在30%以上。

據黑鷹光伏統計,2019年中利集團扶貧光伏電站開工量為113MW,較2018年同期減少了652MW,降幅達85.23%。
除此之外,黑鷹光伏發現中利集團還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財報顯示:截至2019年6月末,中利集團“庫存現金及銀行存款”合計為16.49億元,而它“短期借款”規模達55.15億元,另外其“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指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應付債券及長期應付款)”規模為19.91億元。
9.江西旭陽雷迪
旭陽雷迪成立于2008年6月11日,主要從事太陽能多晶鑄錠及多晶硅片、單晶硅片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擁有三千名員工。生產項目占地近千畝,一、二期位于出口加工區,占地345畝,三期位于城西港區,占地647畝。目前產能多晶1.6GW,單晶150MW,共有220臺多晶鑄錠爐,96臺單晶爐。
作為曾經江西省第二大光伏企業,旭陽雷迪自2018年6月爆發討薪事件以來,不斷被爆出停產、裁員、員工維權、破產重整等新聞,又一光伏巨頭陷入困境。
2018年6月22-24日,旭陽雷迪出現員工集體討薪事件,據員工們反映,公司已經拖欠了員工的4個月工資沒有發,并且自2013年起的5年多時間,都沒有給員工交社保金。由于531政策的出臺,6月份產能減產至30%。
2018年9月起,旭陽雷迪全線停產。2019年1月19日,旭陽雷迪對內部員工發布了公司裁員和破產重整的公告,與全體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并向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破產重整申請。旭陽雷迪不是第一家破產重整的光伏企業,也不會是最后一家破產重整的光伏企業。
10.天龍光電
2019年,8月6日,江蘇華盛天龍光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天龍光電”)發布公告稱,上市公司的3個公司賬戶和1個工會賬戶被凍結,賬戶余額累計超過30萬元。
天龍光電8月6日還發布公告,公司目前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未能獲得市場訂單,前期已承接未交付訂單截至8月6日未取得客戶訂單的具體供貨時間,公司暫未有生產計劃,公司設備制造生產線繼續停產。“目前流動資金持續緊張,單晶硅、多晶硅材料生產、融資計劃均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事實上,天龍光電在2018年便已陷入危局。2018年12月13日,天龍光電發布公告稱,“由于受到行業波動及光伏新政策的影響,公司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的市場需求急劇減少,近期未有新的訂單,導致公司本部生產線全部停產。”并且,“公司停產會對公司現金流和經營性利潤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過去這一年都時間,天龍光電還出現“高管離職潮”,并且開始為了增加流動資金而出售閑置資產。
2019年6月25日晚間,天龍光電稱:“由于受到行業波動及“5·31”光伏新政策的影響,公司生產經營陷入困境,本部生產線全部停產,流動資金持續緊張,上述狀況如不能得到有效改變,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風險。”
7月12日,天龍光電發布的2019年半年度業績預告顯示,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虧損300 萬元至500萬元。最新公告顯示,截至2019年8月6日,天龍光電主要業務設備制造生產線未能恢復生產,停產原因為“公司目前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未能獲得市場訂單,前期已承接未交付訂單截至2019年8月6日未取得客戶訂單的具體供貨時間,公司暫未有生產計劃。”
比如據黑鷹光伏團隊統計,截至6月30日,光伏上市公司總市值為7262.10億元,較年初增加了1585.78億元,增幅為27.94%;又比如8月21日隆基、通威、陽光電源、東方日升等至少7家光伏公司紛紛漲停,其與光伏上市公司股價也近乎全線飄紅;8月28日隆基更是一舉突破千億市值大關。市場普遍認為,引發此次光伏資本紅色浪潮的根由是“光伏旺季即將來臨”。
2019年光伏企業無論在產業端還是資本端的布局確實也都給人一種很兇猛的感覺。比如據黑鷹光伏團隊統計:2019上半年,數十家光伏企業公布了超千億的產業擴張方案,其中單個項目超十億元的重大投資項目就多達27個,擴張領域不僅覆蓋光伏全產業鏈,甚至延伸至風電、水電、半導體等領域;另外2019年上半年至少有35家光伏企業公布了融資方案/計劃,它們計劃融資額近1400億元。
但是,我們縱觀光伏近二十年發展史,光伏產業經歷了幾輪擴張潮,而每次擴張潮都以某個巨頭的倒下而結束,其產生的破壞力甚至將持續數年。當下需要警惕的是,一系列數據證明光伏產業的風險及壓力也在加速聚集:
一方面,201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就超過1400億元,補貼資金缺口巨大及撥放不及時,已嚴重制約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嚴重影響電站投資商的生存與發展。由于光伏電站投資運營商巨額應收款難以快速變現,只能將資金壓力及風險向產業鏈上游層層傳遞,如今巨大的應收款壓力已籠罩整個光伏產業。黑鷹光伏統計發現,截至2018年末,78家主要光伏公司應收賬款及票據規模為1717.67億元,約是它們2018年所創造凈利潤的8.03倍。
這個壓力還在不斷向下傳遞,數據顯示,2018年這78家光伏公司在“應收賬款及票據”規模同比下降的2.45%的情況下,其“應付賬款及票據”規模卻同比增長了6.54%,這或許意味著更多的企業將資金壓力及風險轉移到了中小供應商的身上。
另一方面光伏整體融資環境更是不容樂觀,比如2018年光伏上市公司整體凈籌資現金流僅為157.4億元,較2017年巨降了700.64億元;前十名光伏上市公司凈融資現金流合計為282.54億元,占整體比重達179.50%。如今很多中小企業不僅面臨后續融資難的問題,甚至已經遭遇了“抽貸”的現象,資金壓力已經嚴重影響這些企業生存。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風險和壓力應引起企業的高度重視。截至目前56家光伏企業擔保總額高達約1308.5億元,前30名企業擔保總額都在10億元以上。部分企業已經爆出了擔保危機,企業面臨巨額補償,甚至破產重整危機(詳見下文)。
再回到公司層面,在應收賬款回款難、融資形勢嚴峻等綜合因素下,很多企業都面臨著巨大的短期償債壓力,部分老牌巨頭諸如興業太陽能、海潤光伏等都發生了債務逾期,甚至部分企業被列入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它們面臨著控制權轉讓、退市、破產重組等命運。
為了讓讀者對這些危機及風險有更直接、深刻的認知,我們挑選了10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它們的跌宕興衰,在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進程里代表了不同的企業發展樣本,具有極高的借鑒意義,其中況味,諸君意會。
特別要鄭重聲明的是:黑鷹此次分析這些光伏企業沒有任何嘲諷之意,十年來光伏行業來來去去,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不勝枚舉,很多企業即便一時“失敗”、或陷入困境之中,但其對中國光伏的發展也貢獻了一份力量。黑鷹復盤這些企業是通過分析其“因何而敗”,為讀者提供一個思考的維度,希望引以為戒,這便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初心。
1.昱輝陽光
作為老牌的光伏企業之一,李仙壽創立的浙江昱輝陽光能源有限公司曾頗有名氣。但從去年至今,這家光伏企業顯然陷入了經營困境。
2001年,在開創昱輝陽光之前,李仙壽建立了玉環太陽能能源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商業和住宅用太陽能電池和組件產品制造企業。4年之后,李仙壽才和另外三個伙伴在浙江嘉善姚莊,正式創立了昱輝陽光。或許他們自己都沒想到,這個最初只有150萬美元注冊資本的小公司,日后會創造怎樣的輝煌。可能更沒有想到輝煌過后的折騰與跌宕。
2019年7月8日,浙江昱輝陽光能源有限公司(美股代碼SOL)發布公告稱,李仙壽先生辭去CEO職務(包括在子公司擔任的管理職務),公司同時任命Shelley Xu女士作為新任CEO。公告稱,這位歷經產業跌宕的企業家辭職是由于是“個人原因”。
緊接著,有媒體從全國法院執行信息平臺獲悉,昱輝陽光于7月22日4次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老板李仙壽已被限制消費,執行法院是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昱輝陽光的經營業績到底如何?李仙壽曾表示,未來昱輝陽光要以全球輕資產項目開發模式為戰略,重點關注分布式發電和屋頂太陽能。眾所周知的是,昱輝陽光已于2017年底徹底退出了太陽能組件制造業務。
不過,對于這家企業的轉型與復興,如果系統梳理企業多年來的經營數據,一言以蔽之:壓力重重。
以昱輝陽光2019第一季度的財報為例:營收1310萬美元,環比增長134%,同比下降71%;所得稅和非控制性權益前的虧損為550萬美元;毛利潤40萬美元,環比下降86.2%,同比下降95.2%,毛利率僅為2.8%。目前,昱輝陽光約有1.4吉瓦的太陽能發電項目,其中擁有227.5兆瓦的在運營屋頂項目。
從更長的時間周期來分析,也許我們可以對這家企業面臨的處境看得更加清楚,黑鷹光伏曾梳理昱輝陽光上市至今的部分核心經營數據,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家老牌光伏企業確實陷入了經營困境:





2.興業太陽能
531新政公布以后,有著15年歷史的興業太陽能(0750.HK)成為第一個債務暴雷的光伏上市企業。10月17日,興業太陽能公告稱,其1.6億美元優先票據(年息6.75%)未能如期償付,造成付款違約并觸發另2.6億美元優先票據和9.3億人民幣可轉債的交叉違約。
事實上,在興業太陽能債務暴雷前夕其還發布了一份頗為亮麗的半年報:2018上半年營業收入達30.24億元,同比增長了3.87%,凈利潤為2.28億元,同比增幅185.67%,毛利率也較上一年同期增長3.57%至24.40%;另外其資產負債率也下降了3.01%。
興業太陽能爆發債務危機,主要在于其對現金流掌控力不足。筆者在審閱興業太陽能2018年上半年財報中“現金流量表”及“資產負債表”時發就現諸多有違財務邏輯的地方。
比如在興業太陽能營業收入、凈利潤上半年分別同比增加1.12億元、1.49億元的情況下,其經營現金流凈額卻同比減少了6.20億元至-2.16億元。也就是說,上半年興業太陽能營收、凈利潤雖然看似增長不少,但其并沒有收到真金白銀。
更為嚴峻的是,上半年興業太陽能“籌資現金流”僅為1.04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2.87億元。這是為何?
“經營現金流”、“籌資現金流”一個代表企業自身“造血能力”,一個彰顯企業“融資能力”,興業太陽能兩項能力的巨幅下滑,直接導致了上半年“現金凈增加額”減少了17.26億元。
而看似興業太陽能上半年資產負債率下降了3.01%。但其“短期借款及長期借貸到期部分”增加了14.32億元至42.11億元,這創出了自2009年上市以來19個財報(包括年報及半年報)歷史新高。而截至2018年6月末,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為13.96億元(同比減少了10.64億元)。
“若再加上2019年到期未贖回的人民幣9.6千萬的可轉債,公司的總違約債務約為人民幣30 億。在計入2018 年6月末時的人民幣32.6億銀行貸款后,公司的總債務約達人民幣63億。當前凈債務預計約為人民幣46億。”國泰君安如是說。
如上所述,興業太陽能此次爆發債務危機除了對企業現金流“失控”之外,還與管理層過于樂觀的態度以及缺乏消減負債率的決心及掌控力有直接關系。
早在2016年中期業績說明會上,興業太陽能財務總監余俊敏表示,上半年興業太陽能負債比率為68.8%,集團目標將負債率減至50%以下水平,但進度就要視集團賣電站的進展而定,將優先出售位于西北的電站。
但事實卻是,自2014年至今,興業太陽能資產負債率從未低于60%。而且,即便在2018年半年財報中興業太陽能仍舊表示,“本集團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自建筑合同及材料銷售的應收款項,以及來自電力銷售的收入。”憑借現有現金資源以及從銀行獲取的信貸,本集團擁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來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事實卻是,在興業太陽能發布2018年半年財報26天后,其就爆發了債務危機。
同時,數據顯示興業太陽能也面臨著巨大的應收賬款回款壓力。如表所示,興業太陽能應收賬款及票據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已經連續6年增長,2018年末已經達到75.73%。財報還顯示:截至2018年6月末,興業太陽能“已逾期”應收貿易款及應收票據規模為11.07億元,同比增加了3054萬元,同比增長了2.84%。一些列數據多少說明了興業太陽能對“應收賬款”似乎逐漸失去了掌控力,這也為其債務危機買下了隱患。
2018年財報顯示:2018年興業太陽能營業收入下降了23.56%至44.75億元,虧損了6.79億元,同比下降了572.05%。
1月22日晚間,興業太陽能發布公告稱, 公司第一大股東Strong Eagle與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山東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訂了了諒解備忘錄,水發能源集團將擁有不少于公司發行股份之50.1%。8月26日上午,雙方聯合召開股權并購重組工作說明會,向珠海市政府相關部門及銀行債委會匯報了并購重組工作的最新進展。雙方計劃在10月底前完成交割。
3.海潤光伏
成立于2004年的海潤光伏曾是中國最大的晶硅太陽能電池生產企業之一,公司在國內江蘇、安徽、云南三省擁有六大生產基地,員工總數超過6000人,晶體硅一體化產能位居全球前十。
據黑鷹光伏統計,最兇猛時,曾在一年之內成立(計劃)64家公司,在全國內跑馬圈地;5年計劃投建光伏電站規模合計約為16GW,粗略統計計劃投資總額高達1600億元,彼時的海潤意氣風發,劍指“獅子王”寶座,力圖成為“千億級市值企業”。
然而,現實卻是2012年-2018年7年間海潤扣非后連續虧損,累計虧損達75.16億元,其在2019年7月12日更是以“退市”落幕。
筆者分析認為,海潤之敗在于當時(2011年)對國內外局勢預測過于樂觀,與后勢有嚴重偏差。海潤逆勢進擊、過早布局國內下游電站領域,為后來的敗北埋下了重大隱患;而海潤之敗根本原因還在于其羸弱的資本實力,與帝國野心存在巨大鴻溝。
數據顯示,自2011年-2017年前三季度,海潤凈籌資現金流僅為73.29億元,經營現金流僅為17.32億元,兩者合計也不過90.61億元,僅為上述計劃投資額的5.66%。打仗打的就是錢糧,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持,再好的策略也不過紙上談兵。
據最新財報,截至2019年3月末,海潤光伏“貨幣資金”儲備僅為1.01億元,“短期借款”規模為9.43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規模為13.63億元,其資金壓力可想而知。
另據黑鷹光伏統計,至今海潤光伏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法律案件”共計102件,最早立案時間為2017年8月17日,最近一次立案時間為2019年6月24日,這些訴訟案件累計“執行標的/未履行金額”合計高達384593萬元。
4.英利
英利綠色能源成立于1998年,生于河北保定,公司產品和服務涵蓋了從多晶硅鑄錠、硅片、光伏電池片、光伏電池組件的生產到系統安裝的整個光伏產業鏈。
在苗連生領導下的英利曾被業內視為“價格屠夫”,2007年英利綠色能源在苗連生掌舵下,成功搶灘美國紐交所,市值達22.66億美元,在10家海外上市的中國光伏企業中位列第三。這一年,51歲的苗連生以137.6億元身價躋身《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成為“河北首富”。
2010年,英利還贊助了南非世界杯,成為首家贊助世界杯的中國企業,彼時英利風頭一時無兩,時隔4年后,英利2014年再次贊助了巴西世界杯。
據黑鷹光伏統計,在2007-2016年這十年間,英利綠色能源實現營業收入合計達1021億元,但是,公司自2011年以來卻深陷虧損泥潭難以自拔,6年里公司累計虧損172.16億元,十年累計虧損153.05億元。
這期間英利還爆發了債務危機,比如2015年10月英利子公司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筆超10億元的債務未能按期足額兌付;2016年5月,天威英利發行總額14億元的債券也宣告違約。期間,在銀保監會的指導下,國家開發銀行率領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多家債權銀行組建了英利集團金融債權人委員會,涉及金融債務達到120億元。
2018年6月,英利因“未能在連續30個交易日內保持至少5000萬美元的平均全球市值,且其股東權益不足5000萬美元,不符合持續上市標準”,被紐交所暫停ADS交易。
知名行業專家紅煒老師曾評論道:“2011年以后,英利在光伏加工環節和電站環節連續發力,先是2012、2013年成為全球組件出貨量第一,后是2013年宣布5年時間建成13-15GW光伏電站、進入國內光伏電站建設前兩名,勢必造成負債率過高、資金緊張。”
2019年7月8日英利官網發表了一篇《英利老苗有話說》,在文中苗連生坦言,“這幾年,英利遇到了天大的困難,過得實在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今天就不說這個了。”在此文中,老苗主要是為了表示“感謝”——“感謝黨中央國務院對英利的高度重視和這么強有力的支持!”最后老苗說,黨中央國務院這么關懷民營實體經濟,作為光伏行業咱們就剩下一個字了,干!為責任干,為擔當干。
根據《證券日報》在2019年6月初報道,近日,在國家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光伏企業英利綠色能源歷經3年,債務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據多方了解,其框架性重組方案已形成,并完成向相關部門和國務院報告,將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重組完成后,英利將成為國有控股的企業。
5.順風清潔能源
順風清潔能源早年因以黑馬姿態將破產重組的無錫尚德收入賬下,而名震光伏江湖。在2013年11月順風清潔能源將無錫尚德收入賬下之時,無錫尚德經確認的債權金額便高達107億元。
在有著“光伏圈并購帝”之稱鄭建明帶領下順風清潔能源此后還拿下了德國光伏企業S.A.G、美國光伏制造商Suniva以及LED企業晶能光電。
利潤表顯示,瘋狂的并購雖然讓順風清潔能源營業收入從2012年的10.69億元暴增至2018年的103.27億元,短短六年間暴漲了8.66倍,但是其“扣非后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僅在2014年盈利8906萬元,2015年-2018年合計虧損了558172萬元。
造成這樣的“兩極現象”主要是因為順風清潔能源一系列并購資金主要來自于外部債務融資,據黑鷹光伏統計,順風清潔能源6年間“短期借款”已經從2012年末的90322萬元增長至2018年末的714808萬元,6年時間增長了6.91倍。另外截至2018年末其“長期借款”也增長至391926萬元,其資產負債率已經達到了創歷史新高的85.64%。而截至2018末,順風清潔能源“貨幣資金”僅為75459萬元。
在舉債擴張的策略下,順風清潔能源“利息支出”從2012年的7473萬元增長至2018年的128592萬元,增長了16.21倍,高居不下的利息費已經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在利潤端及資產端均承受重壓的順風清潔能源市值遭遇“雪崩”:五年前(2014年)順風清潔能源市值一度達到260億港元,可如今(2019年8月27日)其市值僅為10.71億港元,巨降了95.88%。
2019年3月,順風光電公告顯示,擬以30億元價格出售旗下江蘇順風光電100%股權,而無錫尚德正是順風光電體系之內。
如今尚德的形勢仍不容樂觀。據黑鷹光伏調查統計,截至目前無錫尚德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涉及“法律案件”共計4件,最早立案時間為2018年5月3日,最近一次立案時間為2019年6月19日,這些訴訟案件累計“執行標的”合計達23517萬元。
6.大海集團
時間回撥到2018年11月26日,山東大海集團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據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大海集團)擔保企業出現問題等一系列因素導致大海集團資不抵債,走上破產重組的道路。”《山東大海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債券2017年年度報告(修訂版)》補充公告顯示,截至2017年末,大海集團為14家企業擔保,對外擔保合計204665萬元。
擔保可以說是民營企業貸款等融資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家遭遇擔保危機的企業老總對中國經濟周刊解釋說:“企業向銀行貸款,可以采取抵押貸款的形式,但局限于抵押物(如土地、設備等)的價值,貸款額度通常較小,難以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如果有其他企業為它做擔保,額度就會擴大,甚至超過抵押貸款額度的10倍以上。通過擔保,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度大大下降,而一旦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為其作保的企業就要履行代償義務。”
需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是,大海集團遭遇的擔保危機并非光伏行業個例。據黑鷹光伏統計,2018年順風清潔能源、航天機電所擔保企業或宣布破產、或債務逾期,順風清潔能源、航天機電需承擔相應的償付責任,金額分別約為26420萬元和2354萬元。
1月21日,向日葵也發布了其擔保的浙江榮盛紡織有限公司等被擔保單位破產清算進展情況,根據《民事裁定書及和解協議》,向日葵對該事項預計計提擔保損失 4757萬元。
而黑鷹光伏統計,截至目前56家光伏企業擔保總額高達約1308.5億元,前30名企業擔保總額都在10億元以上。
目前出現擔保危機的光伏企業都來自于外部擔保風險(對外部企業擔保)。據黑鷹光伏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末約有22家光伏企業對外部企業提供擔保規模為150.31億元(不包括對子公司擔保)。前四名企業對外擔保規模都在十億元以上。
7.科林環保
科林環保原來是家工業粉塵治理解決方案提供商,是國內最大的袋式除塵設備專業制造企業之一,自2016年底開始轉型為光伏電站開發及運營商,2018年其光伏業務實現收入8256萬元,虧損53851萬元,分別同比下降了90.68%和1394.23%。
在“受宏觀經濟及金融政策影響,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年內到期的融資大多未能續貸甚至被抽貸,償還該等融資擠占了公司大量流動資金。”甚至出現部分債務逾期的現象(公司及子公司累計逾期債務合計金額約13288萬元)。
7月13日,科林環保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19年上半年虧損1900萬元-2400萬元(去年同期盈利2819萬元)。
“公司前期已墊資修建的光伏電站未能如期收回墊資款,造成公司運營資金緊缺,同時,受光伏政策以及流動性緊張等因素的影響,較大程度制約了公司光伏電站相關項目的開發、建設規模,從而影響了整體銷售收入、凈利潤的增長,而運營管理費用、折舊攤銷、利息支出等各項剛性支出并未隨之減少,影響本期凈利潤。”科林環保如此解釋道。
黑鷹光伏發現,7月中旬科林環保及實際控制人黎東先生被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并被出具了《限制消費令》。
截至8月16日,科林環保及全資子公司連續十二個月內累計訴訟(在訴)金額合計為 18058萬元,占公司2018年凈資產的90.33%。
財報顯示,截至2019年3月末,科林環保“貨幣資金”僅為5880萬元,其“短期借款”規模為7500萬元,長期借款為9256萬元,其形勢不容樂觀。
作為上市公司科林環保尚且面臨如此境況,其他中小光伏電站開發商又如何呢?
8.中利集團
2011年,中利集團通過并購手段逆勢搏擊光伏行業,當時有人質疑說它“買了個爛攤子”、“逆市進入光伏業接盤嫌疑大”,但中利集團用6年時間硬生生又在光伏領域打造了一艘“百億級”戰艦。
在531新政頒布后,中利集團比較樂觀認為“光伏扶貧電站業務的拓展規避了531光伏新政對公司的不利影響,公司按照既定目標,持續加大光伏扶貧電站業務開發力度,其已成為公司利潤的重要來源。”
在王柏興眼中“光伏扶貧”是其光伏戰略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光伏扶貧確實很難賺錢。但是根據國家扶貧辦估算,每年光伏扶貧的安裝量不會少于2GW。如果中利的光伏扶貧規模真的能上去,我就能把我的組件賣出去。”
然而事實證明,中利集團管理層對扶貧市場的預期似乎過于樂觀了。
要知道早在2018年3月26日,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發布的《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指出,光伏扶貧電站不得負債建設,企業不得投資入股,這使得在資金來源上,光伏扶貧項目只能用政府性資金包括各級財政資金、定點幫扶和社會捐贈資金。
而據黑鷹光伏了解,中利光伏扶貧產業基金為村級光伏扶貧項目提供的是“借入”資金,這個政策對中利光伏扶貧戰略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2018年全年中利集團“由于受光伏扶貧326政策影響,扶貧光伏電站開工數量490MW比預期下降51%。”2018年度中利集團實現營業收入167.26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3.85%。歸屬于母公司凈利潤為-2.88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4.25%。
2019年上半年中利集團營業收入再度同比下降了22.29%至57.35億元;歸屬于母公司凈利潤為1302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73.60%。其中其光伏收入合計為24.18億元,同比下降了38.76%,如下表所示“扶貧電站收入”降幅最大,另外其“光伏組件及電池片”、“光伏電站”收入降幅也都在30%以上。

據黑鷹光伏統計,2019年中利集團扶貧光伏電站開工量為113MW,較2018年同期減少了652MW,降幅達85.23%。
除此之外,黑鷹光伏發現中利集團還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財報顯示:截至2019年6月末,中利集團“庫存現金及銀行存款”合計為16.49億元,而它“短期借款”規模達55.15億元,另外其“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指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應付債券及長期應付款)”規模為19.91億元。
9.江西旭陽雷迪
旭陽雷迪成立于2008年6月11日,主要從事太陽能多晶鑄錠及多晶硅片、單晶硅片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擁有三千名員工。生產項目占地近千畝,一、二期位于出口加工區,占地345畝,三期位于城西港區,占地647畝。目前產能多晶1.6GW,單晶150MW,共有220臺多晶鑄錠爐,96臺單晶爐。
作為曾經江西省第二大光伏企業,旭陽雷迪自2018年6月爆發討薪事件以來,不斷被爆出停產、裁員、員工維權、破產重整等新聞,又一光伏巨頭陷入困境。
2018年6月22-24日,旭陽雷迪出現員工集體討薪事件,據員工們反映,公司已經拖欠了員工的4個月工資沒有發,并且自2013年起的5年多時間,都沒有給員工交社保金。由于531政策的出臺,6月份產能減產至30%。
2018年9月起,旭陽雷迪全線停產。2019年1月19日,旭陽雷迪對內部員工發布了公司裁員和破產重整的公告,與全體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并向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破產重整申請。旭陽雷迪不是第一家破產重整的光伏企業,也不會是最后一家破產重整的光伏企業。
10.天龍光電
2019年,8月6日,江蘇華盛天龍光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天龍光電”)發布公告稱,上市公司的3個公司賬戶和1個工會賬戶被凍結,賬戶余額累計超過30萬元。
天龍光電8月6日還發布公告,公司目前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未能獲得市場訂單,前期已承接未交付訂單截至8月6日未取得客戶訂單的具體供貨時間,公司暫未有生產計劃,公司設備制造生產線繼續停產。“目前流動資金持續緊張,單晶硅、多晶硅材料生產、融資計劃均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事實上,天龍光電在2018年便已陷入危局。2018年12月13日,天龍光電發布公告稱,“由于受到行業波動及光伏新政策的影響,公司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的市場需求急劇減少,近期未有新的訂單,導致公司本部生產線全部停產。”并且,“公司停產會對公司現金流和經營性利潤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過去這一年都時間,天龍光電還出現“高管離職潮”,并且開始為了增加流動資金而出售閑置資產。
2019年6月25日晚間,天龍光電稱:“由于受到行業波動及“5·31”光伏新政策的影響,公司生產經營陷入困境,本部生產線全部停產,流動資金持續緊張,上述狀況如不能得到有效改變,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風險。”
7月12日,天龍光電發布的2019年半年度業績預告顯示,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虧損300 萬元至500萬元。最新公告顯示,截至2019年8月6日,天龍光電主要業務設備制造生產線未能恢復生產,停產原因為“公司目前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主要產品單晶爐、多晶爐未能獲得市場訂單,前期已承接未交付訂單截至2019年8月6日未取得客戶訂單的具體供貨時間,公司暫未有生產計劃。”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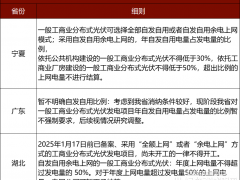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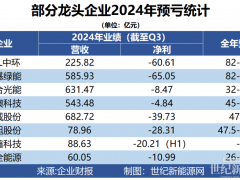


0 條